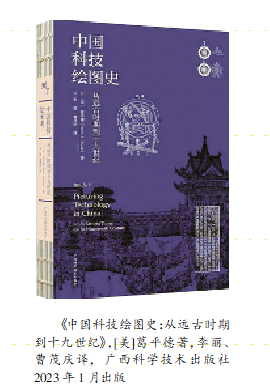
中國(guó)古代本有“左圖右史”的傳統(tǒng),,“圖”能與“史”并列。在一些早期文獻(xiàn),,比如湖南長(zhǎng)沙子彈庫(kù)出土的楚帛書(shū)中,,還是“圖文并茂”的狀態(tài)。但可能是因?yàn)橹腥A文明的早熟,,后來(lái)由文字構(gòu)成的“史”極為發(fā)達(dá),,而且古代中國(guó)人在選擇“圖”的對(duì)象方面似乎頗多拘束,例如我們長(zhǎng)期排斥對(duì)人體的直接描繪(吳帶當(dāng)風(fēng),、曹衣出水等都只是描繪服裝),,最終形成了“圖衰史盛”的局面。結(jié)果是我們保留了非常豐富的文字史料,,圖像資料則相形見(jiàn)絀,,當(dāng)然也不是完全沒(méi)有。
以前每逢出版社要求為與中國(guó)科技史有關(guān)的書(shū)提供圖像資料,,我不得不耐心地向他們解釋,,中國(guó)古代這方面資料比較少,不像在西方美術(shù)作品中尋求西方科技史圖像資料那么方便,。久而久之,,我形成了一個(gè)印象:中國(guó)古代反映科技成就的圖像資料很少,特別是能夠喚起審美沖動(dòng)的那種圖像資料就更少,。雖然我在讀書(shū)時(shí)若有所見(jiàn),,也會(huì)注意收集一些,但很少能解決實(shí)際問(wèn)題,。
正因?yàn)樯鲜鲇∠笞魉?,我差點(diǎn)被這本《中國(guó)科技繪圖史:從遠(yuǎn)古時(shí)期到十九世紀(jì)》的中文書(shū)名誤導(dǎo)了,以為這是一本關(guān)于中國(guó)古代科技史的圖文書(shū),。
一開(kāi)始我披閱此書(shū),,見(jiàn)到書(shū)中大量關(guān)于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的圖像資料,有些是我未曾見(jiàn)過(guò)的,,有些雖曾寓目,,卻從未見(jiàn)被處理得如此美輪美奐——這些處理手法包括裁割、放大,、修圖等,,美術(shù)編輯肯定在此書(shū)的版面設(shè)計(jì)上花了很多工夫。當(dāng)時(shí)還為作者葛平德居然收集了那么多關(guān)于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的圖像資料而稍感驚異,,感覺(jué)上面那個(gè)印象應(yīng)該改一改了,。
后來(lái)看了書(shū)中內(nèi)容,,并注意到原文書(shū)名(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: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),才知道作者是想通過(guò)這本書(shū)告訴讀者,,中國(guó)古代是如何通過(guò)繪畫(huà)來(lái)反映技術(shù)的,。
我不得不承認(rèn),本書(shū)確實(shí)成功地改變了我先前認(rèn)為中國(guó)古代缺少科技圖像資料的認(rèn)知,,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做到這一點(diǎn)的途徑,,他的做法很有啟發(fā)意義。下面稍談幾個(gè)例子,,以見(jiàn)一斑,。
本書(shū)在拓展中國(guó)科技史圖像資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,甚至還在理論上有所思考,。例如作者在書(shū)中提出了這樣一種觀點(diǎn):不管如何界定“從業(yè)者”這一術(shù)語(yǔ),,現(xiàn)存的由技術(shù)“從業(yè)者”繪制的中國(guó)插圖都寥寥無(wú)幾……在中國(guó),很大一部分技術(shù)性圖繪并不以傳達(dá)技術(shù)信息為目的,,或者說(shuō)不以傳達(dá)技術(shù)信息為主要目的,。
這樣的想法富有啟發(fā)性。首先,,這有助于我們拓寬尋找中國(guó)古代科技圖像資料的視野,,因?yàn)橄惹拔覀兞?xí)慣在(被我們認(rèn)為是)“以傳達(dá)技術(shù)信息為目的”的圖像資料比較集中的著作中尋找,而這樣的著作不外乎《新儀象法要》《天工開(kāi)物》《靈臺(tái)儀象志》等有限的幾部而已,。如果我們認(rèn)識(shí)到,,在“不以傳達(dá)技術(shù)信息為主要目的”的作品中,同樣可以找到有關(guān)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的圖像資料(不管繪制者的目的是什么),,那我們的研究對(duì)象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拓展,。
其次,這個(gè)想法有一定的理論深度,,因?yàn)樗⒁獾健皬臉I(yè)者”的界定問(wèn)題,。這個(gè)問(wèn)題之前很可能被許多研究者忽略了。
例如,,《天工開(kāi)物》的作者宋應(yīng)星能不能算書(shū)中所記載的各種工藝的“從業(yè)者”呢,?顯然是不能算的。而《靈臺(tái)儀象志》中的大量工藝插圖,,雖然有不少是從歐洲有關(guān)著作中移植過(guò)來(lái)的,,但考慮到比利時(shí)傳教士、清朝時(shí)期的南懷仁作為那些大型天文儀器(現(xiàn)存北京建國(guó)門(mén)古觀象臺(tái)上8臺(tái)儀器中的6臺(tái))的“總設(shè)計(jì)師”和鑄造工程的“總工程師”的身份,,認(rèn)為《靈臺(tái)儀象志》中的各種插圖是出于“從業(yè)者”之手,,則較為合理。
另外,書(shū)中有一些作者囿于見(jiàn)聞不足而論述不很成功的例子,,但仍然富有啟發(fā)性,。例如本書(shū)第二章討論“比例圖與透視法”的一節(jié)中,提到了中國(guó)佛教的大型壁畫(huà)——這一節(jié)作者主要引用了美國(guó)學(xué)者胡素馨的成果,。
作者認(rèn)為,,這些大型壁畫(huà)在繪制之前,應(yīng)該有比例圖或縮小尺寸的草圖,,但在中國(guó)卻找不到這樣的比例圖或草圖,。作者說(shuō):“我們?cè)诂F(xiàn)存資料(必須承認(rèn),,現(xiàn)存資料極為有限)中并沒(méi)有發(fā)現(xiàn)有服務(wù)于這一目的的比例圖實(shí)例……這一時(shí)期的佛像都體量龐大,,那么在制作過(guò)程中應(yīng)該用到了比例圖,然而,,這方面的現(xiàn)存實(shí)例也沒(méi)有,,甚至連表明使用了比例圖的參考文獻(xiàn)也沒(méi)有?!?/p>
于是,,胡素馨和本書(shū)作者將一個(gè)未解之謎留給了讀者。
其實(shí),,比例圖的想法,,純粹是作者從西方繪畫(huà)實(shí)踐中得到的。本書(shū)作者和胡素馨可能完全沒(méi)有注意到,,從中亞傳入中土的佛像繪制/塑造傳統(tǒng)工藝中,,另有一套奇妙的方法,根本不需要西方人想象中的比例圖,。
這套方法是這樣的:通過(guò)一系列具有固定比例的幾何圖形,,包括直線、圓,、垂直中分線,、對(duì)角線等,就固定了一個(gè)佛像的所有要素,,匠人只需據(jù)此繪制/塑造即可,。由于固定的只是比例,所以無(wú)論需要多大尺度的佛像,,都只要按照同樣的要素制作即可,。我們完全可以將這套由幾何圖形構(gòu)成的佛像要素系統(tǒng),視為一種“萬(wàn)能比例圖”,,它顯然比本書(shū)作者所設(shè)想的比例圖更為先進(jìn),、更為好用,也更容易傳承。
當(dāng)然,,佛教壁畫(huà)是一種特殊題材,,佛像繪制更是一個(gè)特例,通常不與科技發(fā)生直接關(guān)系,,盡管“萬(wàn)能比例圖”本身是富有技術(shù)含量的,。
而與科技有關(guān)的繪畫(huà),比如工藝的說(shuō)明示意圖(可舉《天工開(kāi)物》《靈臺(tái)儀象志》為例),,或是“不以傳達(dá)技術(shù)信息為主要目的”的作品中描繪的科技用品(可舉本書(shū)作者注意到的《清明上河圖》為例),,都不需要繪制大型圖幅,自然也就不存在比例圖的問(wèn)題,。
最后有一個(gè)問(wèn)題,,不知是作者掌握的資料不全面,還是現(xiàn)有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,,本書(shū)主要基于西方的研究成果展開(kāi)論述,,甚少使用論述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繪圖的當(dāng)代中文成果。出現(xiàn)這一現(xiàn)象的原因,,既可能是因?yàn)樽髡邿o(wú)力廣泛閱讀中文研究成果,,也可能是因?yàn)檫@樣的成果本身確實(shí)非常稀少。
據(jù)我個(gè)人的初步判斷,,后一個(gè)原因肯定是存在的——我雖不搞圖像史之類的研究,,至少還會(huì)關(guān)注與中國(guó)科技史有關(guān)的研究成果,但我很少見(jiàn)到論述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繪圖的中文成果,,這可能與迄今為止國(guó)內(nèi)從事科技史研究的學(xué)者尚未對(duì)中國(guó)古代科技繪圖領(lǐng)域投注較多的注意力有關(guān),。所幸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有學(xué)者開(kāi)始了這方面的學(xué)術(shù)研究,例如上海交通大學(xué)至少已經(jīng)有一位科學(xué)史博士是通過(guò)圖像學(xué)方面的論文答辯而畢業(yè)的,。